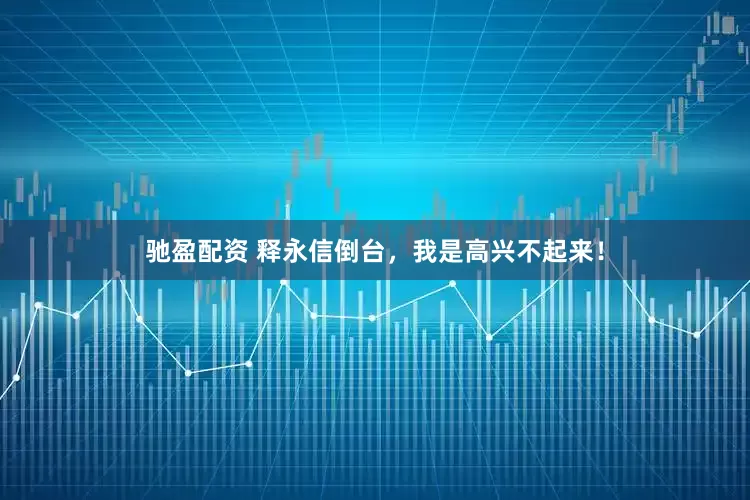
少林方丈释永信被查驰盈配资,闹得沸沸扬扬。急就了一篇发在冰川(《》),标题是老编起的。我和他说,我并不反对“商业化”,这标题容易引发误会。老编笑问“你为何对如此爱护有加?”
“爱护有加”当然不至于,要说多大的恶意,确实没有。写篇“讨释永信檄”的爽文不难,但是犯不着。
01
我不是佛教徒,对大和尚娶妻生子之类的破戒行为无感。这到底是多大罪过,留给其他大和尚评判便是了。至于说少林寺的商业化和由此产生的经济问题,释永信当然是不干净的。但是,“穷庙富和尚”俯拾皆是的当下,他这样的“富庙富和尚”肯定算不上最坏的。何况山门里的纠葛,又没动民脂民膏,喊打喊杀、苦大仇深的满怀义愤是大可不必的。

释永信的舆论口碑一直不好,塌房塌得那么惨烈,无非还是“商业化”的原罪。正经的商业人士动辄获咎,何况是方外之人的跨界经商?
可是,追根溯源,少林寺的“商业化”并非始于释永信,当时的背景下也有不得不“商业化”的苦衷。
若要较真“自古以来”,那寺庙道观自古以来都有经营活动。开发山林、经营田产,都是常规操作。阔气一点的,还搞放贷。唐代尤为盛行,称之为“香积贷”。本金称为“功德”,利息则称“福报”。这在《长安的荔枝》中有专门的描述,并非虚构。
很多名山古刹的繁荣都是一代代僧侣经营的成果,甚至因为经营得太好了,引发了祸事。历史著名的“三武灭佛”,并不是朝廷和佛陀有多大仇怨,都是寺庙的钱多人多惹了祸。
因此,少林寺的商业化并不是当代的发明。反而是寺院经济的破灭,是49年后的一次次改造和运动。庙产中的占比最高的土地,或土改分掉了,或国有化易主了。“地主”是肯定干不下去了,经营商业更无从谈起。佛门从此“清净”?那倒也没有。金身终究是泥塑,也躲不过特殊时代的冲击。总之,到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少林寺和很多名山古刹一样,都是一副颓败的光景。
02
少林寺涉足商业,也是情非得已。而且,少林寺的跨界破圈并非始于释永信。1982年,一部电影和一个人,让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。电影是李连杰的荧幕首秀《少林寺》,人是“武术大师”海灯法师。少林寺因此成为改开后第一代旅游热点,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。1981年在少林寺出家的释永信驰盈配资,和电影《少林寺》、海灯法师显然都没有关系。

可是,旅游热带来的经济收益,大头并不是寺庙的。当年的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,这是归地方政府文旅部门管的。因为,庙是和尚的,山是地方政府的,“寺地关系”的恩恩怨怨持续多年。比如,各地的寺庙景区门票定价高曾经饱受诟病,游客都骂和尚钻到“钱眼里了”,其实是很冤的。钱不是交给庙里的,但锅是和尚们背。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少林寺多次商业化风波中也屡次发生。
比如2010年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少林寺上市风波”,释永信被网民骂的狗血喷头,不得不公开表示“少林寺永不上市”。其实,“上市”的传闻和少林寺没有关系。那是地方政府和香港企业搞了个合资企业,由地方政府授予了该公司景区门票和停车场的四十年经营权,并不涉及少林寺本体核心资产。
其实,少林寺这样的宗教机构,压根就不可能上市。地方政府做不到,释永信也不行。因为中国的宗教机构管理很复杂,产权归属、管理权限都很模糊。普通的商业经营都难以正常开展,连正式的商业合同都很难签,遑论上市这样的高难操作。
03
宗教机构的特殊管理机制下,少林寺的商业化运作自然也是特殊的。比如,释永信名下有18家“少林寺相关企业”的股份,理论上并非他的个人财产。因少林寺并非法人无法办理入股手续,所以由他个人“代持”。理论上讲,释永信不能参与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享受分红。但是,这些“理论”也仅仅是理论而已。实际上没有机制约束他的行为。
寺院的管理机构是寺管会,而寺管会是由主持、班首等主要管理人员和部分居士组成的。这意味着释永信只要能掌控主要管理人员,再有居士的提名权,偌大庙产就是他说了算。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,外部监督也仅有宗教管理部门。这样高度封闭的“内部人体制”,本质上只对上负责。这套机制完全是为了“控制”设计的,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,可想而知。但凡不是真佛,不出问题才奇怪。
2015年,少林寺闹出了著名的“师徒反目”,释永信最倚重的弟子、武僧团总教头释延鲁反戈一击,线上线下揭发了一大堆释永信的劣迹。当时的官方调查组一一为释永信洗白,独独留了一个“存在财务漏洞”的尾巴。可以想见,少林寺的账是真查不清。
释永信在少林寺的商业活动中清白吗?显而易见不是。但是,少林寺的商业运作却是成功的。
04
2015年,释永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承认,成立武僧团、实业公司、药局这些都是商业化行为。但做这些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?假武僧打着‘少林’旗号全世界招摇撞骗,假的‘少林药方’、‘少林产品’满天飞,连‘少林寺’牌火腿肠都出来了。难道我们出家人就得眼睁睁看着一千多年的古老文化这样被人糟蹋?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商业化行为消除这些商业化带来的消极影响,弘扬真正的少林文化。”

他还举了一个例子,“为了阻止少林寺的形象变成一个过分商业化的景点,我们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的。2004年前,寺门前是一条商业街,我们用寺产将这上万老百姓搬迁并重新妥善安置,花了好几个亿。要是我们真的一切‘向钱看’,会干这样的傻事吗?”
他这番表白中有多少真心,无从判断。但是,其中很多事有迹可循。想吃“少林饭”且吃相更难看的,大有人在。
我去过少林寺景区,平心而论,在中国诸多景区中,少林寺景区还真算不上“过度商业化”。武僧表演区、商业区集中在景区外围。寺庙核心区域称得上十分清净。古建筑和文物基本上也是原汁原味的古意盎然。与很多宗教景区里里外外都是算命、拉客的相比,少林寺还算是好的。
这当然不能证明释永信经营有方,但是也确实可以称得上吃相没那么难看,至少可以眼不见为净。
抛开宗教身份不谈,释永信其人其行,与改开初期的首批企业家并无不同。野心勃勃、长袖善舞、精明强干,却又粗鲁无文、私德不谨、德不配位。
这种共性不难理解。能在“商业即原罪”的主流风气中逆流而动、走上商业道路,多少都有些逆天改命的倒逼因素,能是什么“好人”?社会变革总是从边缘开始松动,为“社会边缘人”创造了很多机会。
崛起于边缘的“野蛮生长”能否修成正果,则需要好的制度环境保障。这是少林寺的宗教管理体制无法实现的。这套以“控制”为唯一目的的机制,容不下多少“发展”的空间。还有微妙复杂的“寺地关系”掣肘,更走不了多远。
释永信的倒掉,不值得庆祝,却值得深思。
红腾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